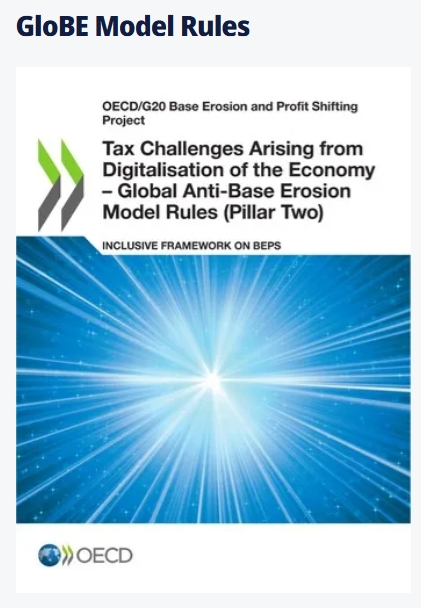本篇是我在東吳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與會計師全聯會主辦,第十六屆稅務實務問題研討會,2025/10/3下午,主題報告所發表的文章-「國際稅法上「雙支柱方案」的最新發展
-全球數位稅、最低稅負制、貿易衝突與折衝」,其中的第二部分-Pillar 2全球最低稅負的報告內容所整理:

全球最低稅負制,實際內容跟您想像的,完全不一樣
這部分要談的是全球最低稅負制(Global Minimum Tax, GMT),也就是 Pillar 2。關於 Pillar 2,新聞中常見的說法是:財政部為了接軌國際、避免台商跨國企業稅基被他國攫取,將推動兩項措施——
-
短期內把 AMT(國內最低稅負)徵收率由12% 調高至 15%,且僅限超大型公司(全球年收>7.5億歐元);
-
長期導入 OECD 版的 GMT (全球最低稅負制)。
財政部的敘事顯然與現在國際進行式以及許多國家思維並不一致。其他國家往往先評估:加入此一國際聯盟或倡議,對本國究竟是加分或減分?究竟可以增加政治利益,抑或是財政利益?就我所觀察,國際間多數討論最終仍回到財政利益的盤算。
基於時間,我從較簡潔的角度說明。今年 2 月,川普表示:「我們不玩了!拜登談妥的內容要重談,我們不玩你們的全球最低稅負 15% 。」這裡需要補充的是:我們以為的 15% 是「所得稅費用/稅前淨利≥ 15% 」,實際上卻完全不是如此,新聞的表述往往不是很完整、正確。
首先,若細讀 200 多頁技術文件,常常腦裡浮現的三個字:「看不懂。」一方面或許是文件艱澀,另一方面,即使我在國際場合請教許多專家學者,他們也坦言「很努力讀過,仍舊太過複雜,欠缺可操作性」。原因之一是其中有許多除外條款與調整項目與 IFRS (國際會計準則)表述相近,且主觀判斷性強,導致大量個案判斷。在各國稅局都擁有裁量空間下,判斷自然會傾向本國的財政利益。
除了除外與調整項目很多、且細緻,留下相當大的主觀判斷空間之外,當初為了調和各國利益促使談判成功,Pillar 2 制度設計中安插了許多後門。我們一般直觀計算稅捐實質負擔率 15% ,會使用所得稅費用作分子、稅前淨利作分母;但是 Pillar 2 在計算15%的負擔率時,會對稅前淨利與所得稅費用都進行調整,尤其有 SBIE (實質經濟活動除外所得,Substance Based Income Exclusion),對實體投資與薪資支出可作一定比例的減除。在這種調整下,許多所得會被排除、費用會被加計,使得Pillar 2 計算個別企業在地的實質稅捐負擔率,最終會比原先預期的更高出一些,更進一步減少跨國企業適用的情況。
我在去年在東吳研討會報告時,有特別指出:官方宣導資料似乎完全沒有提及這些排除條款與調整項目。就我初步檢視的結果看來,台灣某些金融機構——特別是大型的壽險公司——在 Pillar 2 框架下很可能被排除;但若改用 AMT 計算,卻不會被排除要額外加徵稅款。所以貿然將AMT的徵收率由12%調漲至15%,很容易導致打擊錯誤對象的情況。對此,當時財政部至今仍然不表示意見,我認為這一點非常值得釐清。
美國單邊策略:GILTI 與Side-by-Side 並行機制豁免美資企業 但惹毛他國
另一個關鍵在於美國採取的單邊簡化路徑。我解讀美國官方立場是:「務求企業執行簡便、務求聯邦稅收實質增加。」因此推出 GILTI (全球低稅負無形資產所得,2017)稅制,以較為簡化的公式計算美國企業海外所得。相對而言,OECD 全球最低稅負的難點在於:跨國企業所在的每一個國家都要計算一次 15% 實質稅率。以 Google 為例,需計算一百七、八十多個國家,合規負擔極其沉重。也讓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成為最大受益者(中小型事務所沒有機會)。有趣的是,德國最大的軟體公司 SAP 為 Pillar 2 砸下重金打造合規系統,與 Deloitte 合作;若 Pillar 2 推不下去,這些投入恐須認列損失,頗耐人尋味。
美國秉持「簡便與實收」的路徑,先有 GILTI ,隨後在7 月初又以所謂的「大而美法案」(OBBBA)更新為 NCTI 。新舊制度架構相近,只是把參數做了調整而已:過去海外實體投資、已納稅額可在國內減除,現在不准或調降;意在鼓勵把海外實體投資移回美國。某種程度,美國以此方式處理了美資企業的涉外稅制問題,並藉此覆蓋其 CFC (受控外國公司) 規定。
接著,美國以此與 G7 協商,促成所謂 Side-by-Side (並行機制):也就是我們美國政府、美資跨國企業就只要玩我們的 GILTI/NCTI 稅制就好,美資跨國企業報完GILTI/NCTI,跟我們美國政府繳完稅之後,就算結案了;非美資企業就去玩你們的Pillar 2。也就是說 Google、Facebook一旦報繳完美國的 NCTI 稅,他國就不得再重複課徵。
上述美國與OECD的並行機制機制看似簡單,川普也接受。原本他在「大而美法案」中有加入 899 報復條款:若他國對美資企業課最低稅負,美國就對該國施加報復性關稅。但在「並行機制」作為談判折衝後,美國與G7及OECD官方迅速達成協議,也就「暫時」撤回了899報復條款。
協議達成後,OECD 他國普遍不滿:為何美資企業可迴避雙重合規,其他國家與企業卻要逐國計算、購買昂貴軟體、向四大支付高額顧問費?這些額外支付的昂貴成本並不會增加實質生產力,只不過擴張了合規產業鏈而已。
各國紛紛設立「後門」來抵銷「15%最低稅負」 租稅天堂或成為最大輸家
另一個現象是各國紛紛依照OECD Pillar 2的機制,堂而皇之地設置「後門」。以新加坡與越南為例:
-
新加坡:面對最低稅負制的衝擊,為了「接軌國際」又維持投資吸引力,採取「先補足至 15% 、再以現金補貼返還差額」的操作。簡言之,形式上繳到 15% ,但政府透過補貼讓企業實得仍接近原有效稅負。
-
越南:國會已經通過立法,將徵收到的稅金設立特別基金,對受影響的外資提供定向補貼。
-
愛爾蘭與瑞士部分州政府:亦計畫採取現金返還與設立類似基金的作法。
這導致未來Pillar 2的實施會呈現十分弔詭現象=>多數跟進國家在制度上打開後門,真正承受壓力的反而是那些「鳥不生蛋」的國家,例如 BVI (英屬維京群島)與開曼群島、薩摩亞等傳統稅務避風港地區,因其缺乏產業腹地與政策工具,將迫使大型企業逐步遷離。從這個角度看,Pillar 2 的實際政策目的正是壓縮傳統租稅天堂的生存空間;但其附帶影響,是大量的合規成本與人力負擔落到跨國企業與各國稅務機關身上。
對台灣的啟示:不要盲從,先算清楚看清國際風向後再行動
綜合以上分析:若未充分掌握制度細節與外部風險,就貿然喊出「接軌國際」,恐怕是低估了議題的複雜度。尤其自從美國推動 Side-by-Side 併行機制後,國際間幾乎一面倒地認為應重新評估Pillar 2,甚至德國總理與國會議員等也不斷地質疑「德國要不要繼續跟進」的問題。這是非常值得留意的趨勢。
換言之,我們應該避免盲目跟隨。更務實的作法是:先釐清、先估算、再決策——對本國產業別、投資結構、租稅協定網絡、跨境服務型態與外交風險進行情境推演與量化試算,審慎評估加入(或調整)後的實質利弊,再選擇最合適的政策路徑。特別是在當前政治變動加速的情勢下,五個月後的川普是否仍與今日立場一致,都很難預料。
我在此作結。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