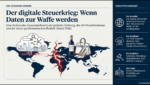本篇是我在東吳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與會計師全聯會主辦,第十六屆稅務實務問題研討會,2025/10/3下午,主題報告所發表的文章-「國際稅法上「雙支柱方案」的最新發展-全球數位稅、最低稅負制、貿易衝突與折衝」,其中的第一部分-Pillar 1全球數位稅的報告內容所整理:

一、前言
簡單來說,支柱一(Pillar 1)與支柱二(Pillar 2)有更親民的稱呼,分別是全球數位稅(支柱一)與全球最低稅負制(支柱二)。這兩項制度設計都帶有強烈的理想性,被納入 BEPS(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行動方案的第二階段延伸內容(第一階段共有 15 項行動方案),具有承前啟後的制度性體系。
然而,這場國際租稅改革的推進歷程,儘管歷經長時間醞釀與多邊討論,至今仍遭遇重重阻礙。這些困難大致可分為內生性挑戰與外部性挑戰兩類。內生性挑戰在於兩大支柱本身的架構極為複雜。其規則設計如同龐大的數學公式,稍有參數調整,就可能導致分配結果出現差異——小國的稅收被壓縮、大國的稅收增加,或使部分數位強權國家流失稅基。這使得各國間的協商過程冗長且艱難。
外部性挑戰則主要源自政治因素。各方好不容易在談判中磨合出勉強的共識,甚至對關鍵爭議條文採取模糊化處理,但就在今年 2 月,美國前總統川普重新上台。他在上任首日便宣布,過去拜登政府對支柱一與支柱二的承諾自此不再適用,並表示將重新設定國際稅制規則。這一舉動使得多年來的努力再度被推翻。
乍看之下,這些發展似乎發生在地球的另一端,與我們距離遙遠。然而事實並非如此。以現代交通而言,十幾個小時的航程便能抵達歐美,說遠不遠、說近也不近;以此比喻說明,全球稅制改革與台灣息息相關,尤其是支柱一。
二、支柱一:數位經濟下的新課稅挑戰-數位稅/數位服務稅
為什麼支柱一與我們的生活關係密切?以我自身為例,我目前每月各支付 20 美金訂閱 ChatGPT 的 AI 服務,許多在座的朋友應該也一樣,因為它的翻譯與語言模型極具實用性。問題在於,我們繳納的這筆費用究竟是付給台灣公司,還是美國公司?答案是後者。那麼,這家美國公司是否應該在台灣繳稅?這就取決於它的登記地點與營運方式。
同樣地,我也訂閱 Google 的 Gemini 服務。不同的是,Google 以新加坡公司名義向我收費,因此,其適用的稅制與登記在美國的 ChatGPT 並不相同。
若以 ChatGPT(美國公司) 為例,依照台灣的跨境電商課稅規則,它需在我國申報「境內利潤率」與「貢獻度」,以此計算應納稅額。這正是數位稅與數位貿易所關注的核心議題之一。
三、台灣的現況與國際認知落差
日前,財政部長在立法院被質詢時,被問及「台灣是否課徵數位稅」。部長斬釘截鐵地回答:「台灣沒有課。」從國內法角度而言,這樣回答並無錯誤,因為我國確實並未明定「數位稅」或「數位服務稅」這一名目。然而,問題在於,國際社會所稱的數位稅,並非僅指「名為數位稅的稅目」,而是包括對跨境數位交易所得進行課稅的任何制度性安排。若從這個角度觀察,台灣現行的跨境電商課稅實務,在美國眼中,極可能已被視為「實質上的數位稅」。
因此,我在論文的前半部針對 Pillar 1 特別強調,現階段應主動釐清、正視的課題正是: 我們課徵的稅與國際上所稱的「數位稅」在法律形式上或許不同,但在經濟實質上卻有重疊。這種認知落差,可能在未來的國際談判與貿易爭端中帶來隱憂。
四、我國跨境電商營所稅稅制與OECD全球數位稅的Amount A
在支柱一的設計中,重點不在繁瑣的細節,而在理解其核心概念。其架構包含兩個主要部分:Amount A 與 Amount B。
- Amount A 的核心是「重新分配大型跨國企業的超額利潤」。所謂超額利潤,通常指企業淨利率超過 10% 的部分。 並非所有數位企業都能達到這個標準,例如 Spotify 直到去年才首度轉虧為盈,前幾年都不屬於適用對象。
- 同樣是AI電商,Google 已經有超額利潤;但 ChatGPT(OpenAI) 目前雖然仍在虧損,主要因為其投入大量 AI 設備折舊成本,包括 NVIDIA 與 TSMC 的硬體採購支出,但依照我國數位電商營利事業所得稅的估算方式,OPEN AI仍可能被視為應稅企業。
根據我國財政部公式的推算邏輯,會假設一定的境內貢獻度與利潤率(例如利潤率約 30%,貢獻度 50% 或 100%)作為計算基礎。這樣的設算方式,形式上與「擴大書審制度」極其相似。若從美國貿易談判代表的角度來看,即使 OpenAI 實際上虧損,仍需在台灣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的話,我國這種稅制設計便可能被解讀為「變相的數位稅」。
五、台灣的數位電商課徵營所稅機制有違反租稅法律主義的嫌疑,成為談判弱點
另外需要再次指明的是,財政部是透過「外國營利事業跨境銷售電子勞務課徵所得稅作業要點」來要求外國的跨境電商需要自行申報並繳納公式型計算的營所稅,而所得稅法73條第1項規定,「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之營利事業,…如有非屬第八十八條規定扣繳範圍之所得,並於該年度所得稅申報期限開始前離境者,應離境前向該管稽徵機關辦理申報,依規定稅率納稅;其於該年度所得稅申報期限內尚未離境者,應於申報期限內依有關規定申報納稅。」一方面營業稅法已經將登記有案的跨境電商當作是在境內沒有固定營業場所的營業人,另一方面跨境電商藉由線上、平台銷售電子勞務,實體上也沒有派人入境,自然就沒有所謂「離境」與否的問題。
簡單的說,財政部的作業要點顯然有違反所得稅法明文規定的疑慮,而違反租稅法律主義正可成為貿易談判對手好好利用的談判弱點,輕則被要求廢止,重則被借用來塑造我國不注重稅捐法治的負面形象。
六、Google 與新加坡架構:典型跨國企業的稅務規劃/避稅安排
另外來說,我們在制度上反而「便宜了」Google。由於Google的廣告與AI相關業務是由登記在新加坡的子公司,以跨境電商模式向我國境內營運,因此可援引《台星租稅協定》第 7 條主張: 提供 Gemini 訂閱服務 的新加坡公司在台灣並無常設機構(PE),因此無須在台灣繳稅。這意味著台灣的稅基實際上被轉移至新加坡課稅。而新加坡是否課徵、或如何課徵,我們並不清楚,但極可能採取寬鬆處理。
值得注意的是,依照經濟部公司登記資料顯示Google 集團 在台灣仍設有三家子公司與一家分公司,但其獲利性業務卻透過合約安排轉移至新加坡進行,這無疑是一種典型的跨國稅務規劃。
我個人是認為這應當是特意的避稅安排,曾經就教一位財政部高官,她卻認為:「Google很早就登記跨境電商了, 怎麼可能利用新加坡公司來避稅?」這般寬容的觀點顯然低估了這些跨境電商在國際租稅規劃上的精明。
台灣雖然不是OECD會員國,數位稅問題也因貿易談判而無從置身事外
以上這些現象提醒我們,我國稅制的實際運作中,我們的稅制與政策實踐,早已與全球稅制改革議題緊密相連。支柱一與支柱二不只是「國際議題」,而是將直接影響台灣企業競爭力與稅收主權的重要變數。所以我們必須密切注意:數位貿易勢必會成為貿易談判中被觸及的議題。
我國表面上看似與 Pillar 1(支柱一方案,全球數位稅)無緣,因為我們不是 OECD 成員,也未參加 Inclusive Framework(包容性框架),雖然表面上我們與 Pillar 1 無直接連結,但實際上,我國現行作為是否會被其他國家認定為「你其實就在做這件事」?美國有 301 調查機制,一旦不幸被調查,結果很可能顯示:我國制度與其認知的數位稅高度相似,僅有一點不同——我們的門檻很低,設定跨境電商年營收60萬以上才適用,屬於普遍性門檻;除此之外,其他設計多有相似之處。因此,若未來媒體報導數位貿易爭議,很可能就與此相關。大家可以對照我上述觀點,觀察其與川普貿易談判立場是否一致。